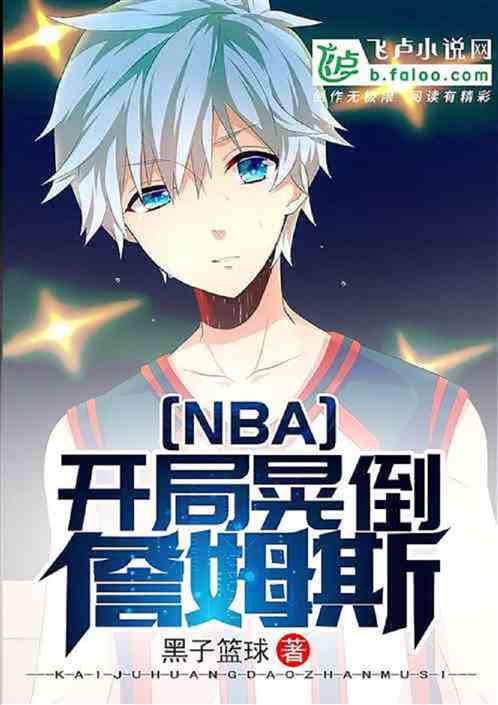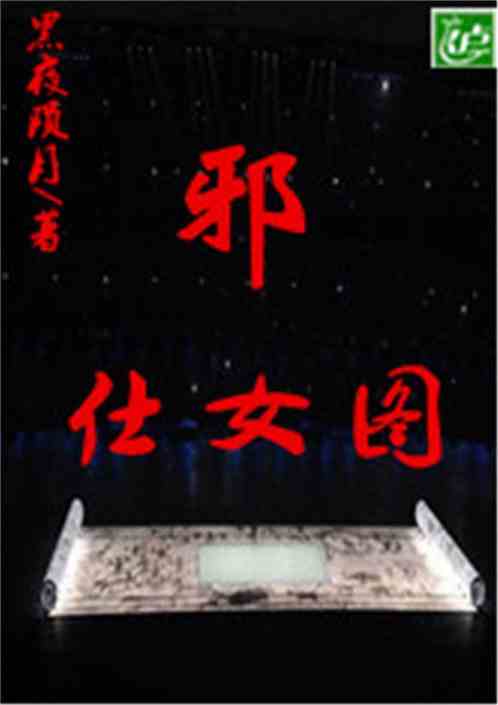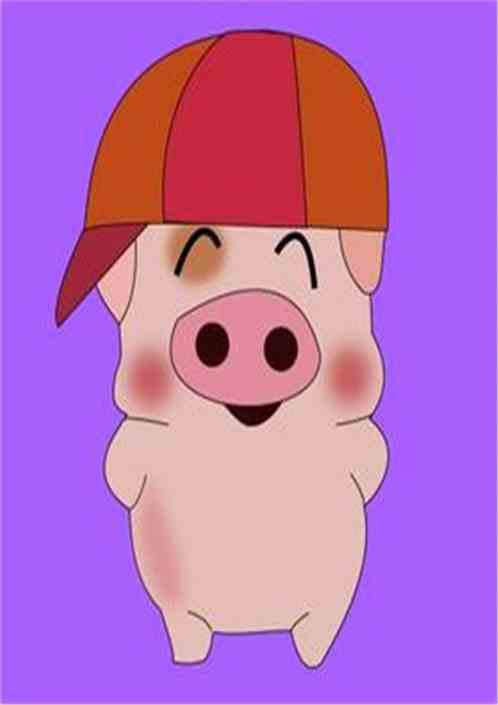在城墙的上侧,迎着寒风迎风招展的旗帜正在燃烧,落下的部分化作点点火花被冷风带走,散落满墙。
数万人的喊杀声震得天地都在颤抖,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火炉上滚烫沸腾的金汁散发着浓烈的恶臭,守城的士兵将滚烫的金汁倒进城门,正在爬上阶梯的士兵被金汁淋透,暴露在外的皮肤瞬间发涨起水泡,然后阵阵发涨,士兵们在一声凄惨的嚎叫后倒下,又倒在墙根上,躺在地上抽搐着。
无论城墙之上还是之下,到处都是穿着黑色皮甲的士兵尸体,到处都是深红色和黑色的血迹。鲜血泛着红色,像恶魔眼中嗜血贪婪的眼睛,从地狱的深渊望向人间。到处都是尸体,许多尸体被肢解,一些失去了手臂,一些失去了头。
燃烧的火焰四处散开,敌人的投石机不停地向城墙投掷火球和石弹。一些火球落入城市,点燃了房屋。火星满天飞,无辜的人四处逃窜。偶尔会有一两个火球落在城面上,炸死守城的士兵,或者点燃士兵的衣服。来不及抢救的人会被活活烧死,燃烧的尸体散发出令人作呕的焦灼气味,逼真的画面构成人间炼狱。
一名身穿铁萨格勒布盔甲的将军倒在七八具尸体中,其中大部分是敌人。鲜血浸透了萨格勒布将军的盔甲,四瓣头盔掉落在一旁,已经扭曲变形。他的脸上满是已经凝固的血,看起来很黑。他周围的士兵一片惊慌失措!
一个士兵惊慌地喊道:“陈都统被石头炸弹打死了!”这一段城墙的防守已经很乱了,但是梯子上的敌人还在爬。虽然马面上有弓箭手向他们射击,但也只能延缓敌人爬城墙的速度。如果这种混乱持续下去,敌人进攻城墙是迟早的事。
这时候,一个将官冲了过来,拿刀痛打那个惊慌失措的士兵,就像一个刚刚登基的狼王,正在收拢他的狼群。将官骂他:“给老子滚回战位去。谁要是把土豪狗放上去,老子就把他和土豪狗一起扔下去!”
在他的压力下,混乱的队伍又开始变得有序起来,战士们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滚石不停地砸向敌人。
将官看了看躺在地上死去的陈笃同。他的眼神看起来很复杂,有同情,有轻蔑,也有感激。
他招呼着那些抬着尸体上城墙的平民,表情凶狠地说:“把将军的尸体拿下来给老子,告诉你们,他是你们灵武城的神。恭恭敬敬的扛下来,小心晚上弄死你!”
将军对他们做了一个异常凶恶的鬼脸来吓唬他们。这一举动着实把他们吓了一跳,身体颤抖得像沉船一样。将官不理他们,匆匆忙忙的下一章去了。
年轻的平民战战兢兢的问道,“吴叔叔,这是...真的是他?”
这位名叫兀术的平民也战战兢兢地说,“我...远远地见过他一次,只是...是他!幸运的是,他...已经死了!”
两个平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抬将官的尸体,但是太重了。他们一时没有抬起来,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死去的将官居然动了一根手指。
在他的梦里,但这不是梦。这是过去记忆的片段。一双美丽的眼睛淡淡地看着他。“我真舍不得你...我从来没有和你分开过这么久……”
他穿着警服,紧紧地抱着她。他心中充满了内疚。他知道自己用了太多力气,伤害了她,但还是不想放手。他真的很想把她融进自己的身体,这样他就可以一直带着她,但这是不可能的。他必须离开。......
“小蓝!”
“哎!”年轻的平民很惊讶,“吴叔叔,你听到了吗?”
“听到什么?”
“杀神叫了个名字!”
五叔没好气骂道,“龟孙,你大白天说什么胡话?小心杀神,晚上来找你要命!”
年轻人也认为自己可能听错了,自我安慰道,“我可能饿了,饿得浑身无力,脑子嗡嗡响,我觉得是耳鸣!”
吴叔叔没好气地说,“还不快点抬。等会儿军师回来,看见我们拖后腿就给我们一刀。”两个人开始想尽办法搬动将官的尸体,但是刚一抬上去,就不堪重负,将官的尸体又倒在了地上。
吴叔叔说:“可以多叫两个人……”
“小蓝!”
这一次,两个人都听到了,吴叔叔大惊失色地喊道:“作弊...欺骗...作弊!”他们尖叫着逃跑,连滚带爬。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捂着头上的伤口,跌跌撞撞地走着。他用头轻轻碰了碰伤口,看着手上的血,眼神迷离。凝结的血遮住了他的视线。他用另一只手擦了擦。他高兴地说:“我没死。他救了我吗?”
他用手擦了擦脸上的血,却觉得越来越糊。“为什么这个人不救我,不帮我把血擦干净?好难受。”
他抬起手臂,试图用袖子擦去血渍,但只擦了脸就觉得又冷又痛。他睁开眼睛,看到了自己手臂上的钉板。“卧槽,这是什么意思?”他迅速看了看自己,发现自己穿着厚重结实的盔甲。
他猛地环顾四周,沮丧地发现自己置身于古代战场。迎接他的是血腥的战斗场面。一支箭射穿了一个士兵的脖子,然后直挺挺地倒下,身体在地上挣扎了几下就死了。
一根长矛刺穿了一个爬上城墙城垛的士兵的胸膛。这名士兵吐出血和泡沫,显然刺穿了肺部。矛拔出来了,士兵仰面栽在墙上。
他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布满血丝的眼睛奇怪地环顾四周,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恐慌。
他的复活让他周围的士兵大吃一惊。要不是看惯了战场上的厮杀和血腥,他会以为这是一具假尸体。
“陈都统没死!”一名士兵惊讶地喊道。
战士们一个个看着,脸上都很激动。然后很多士兵大喊:“陈都统还活着,陈都统还活着!”
他是陈安生,命运又给了他一次机会。他活了下来,但是在另一个世界,一个古老的世界,一个正在进行激烈攻城战的城市!
他记得自己已经死了,死亡的感觉记忆犹新。
突然扔进来一颗手雷,刚好擦着小女孩的侧脸飞了进来。不明物体的出现把小女孩吓得一愣,愣住了。
陈安生感觉前世发生的事情就发生在最后一秒,前世的最后一个画面就像有纸的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
“爸爸!爸爸……”一个小女孩从后面跑了进来陈安生。
当老板看到小女孩时,他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是世界上最有爱的笑容。
这时突然扔进来一颗手雷,正好擦着小女孩的侧脸飞了进去,不明物体的出现吓得小女孩停了下来,站在陈安生旁边。
“小乖乖.....”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大惊失色,想跑过去保护小女孩。
危急时刻,陈安生郝毫不犹豫的抱起小女孩护胸,背对着手雷。手榴弹在落地的瞬间爆炸,冲击波将男子推倒,重重地砸在地上。
手榴弹爆炸的碎片进入陈安生的后脑勺。
我记得他临死前对那个人说了一句话,“不管是军人还是警察,第一任务是救人,不是杀人。”
“陈都统!”那个叫什么龙的在旁边陈安生喊道,“是陈在指挥吗?你没事吧?”
陈安生猛回头看这个名字。真没想到,竟然是陈安生满脸鲜血,双眼布满血丝,盯着这个名字在等待了一会儿。这个面部表情非常狰狞。
“你是谁?”陈安生问道。
何排长一愣,莫名其妙地吃惊,回道,“我.....我是段烈鹏,总指挥什么龙!”
“我.....”陈安生暂停。陌生的环境让他更加警觉。他不能胡说八道。稍作思考后,他问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总司令,你刚刚被石头炸弹的碎片击中头部。所有人都以为你死了,几乎出故障了。幸好马总司令来断后,我第10营才没垮!好在总司令只是昏迷,大家又有了希望!现在敌人暂时撤退了,但估计我们还得根据敌情再来一次。”
“那马杜通呢?”陈安生我忍不住随口问了一句,随即补充道:“头还疼,脑子嗡嗡响。”
段烈鹏马上说道,“是下属们考虑不周。我马上给军医打电话。”段烈鹏起身跑去找军医官,不一会儿就匆匆带着一个扛着医药箱的人进来了。
在军医包扎陈安生的同时,段烈鹏继续说道,“是一营的指挥官,马武马度通。虽然马度通总是和你过不去,但这次我们两个营一起镇守南门,马度通相当坚决。”
陈安生段烈鹏夸完马度通后,笑着说:“那我以后还得感谢马度通!”
陈安生的笑容看在段烈鹏眼里,惊在段烈鹏心里。他认为军队中的将军通常在战斗中很有侵略性。你有什么可感谢的?他以为上官是在讽刺,连忙单膝跪下,双拳低头道:“陈都统,属下没有阻拦,惹怒了他,要他赔罪。”
这一刻,Jean 陈安生愣住了,心想自己说的好好的,怎么会认错呢?他觉得有点意外,突然想了想,马上明白了原因,只好硬着头皮说:“你的工作可以做,交给军医官就行了。”
段烈鹏施了一礼,若获大赦,便唱“诺”而退。
陈安生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无论眼前的场景多么震撼,他都要尽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将军,在危机时刻保持一个古代将军的本色。稍微控制了一下自己凌乱的思绪后,他抬头看着眼前的古城。宽阔的城面一直向前延伸,喧嚣的人群挡住了视线。城内一排排古老的砖石建筑向远处延伸,一直延伸到远处隐约可见的北门城墙。
然而似乎只有南门有烟升起,这让陈安生不禁疑惑,“攻城只攻一面,这是什么战术?
古代的战争将领宁愿在战场上作战,也不愿攻城,因为攻城是一项技术活,会对进攻方造成重大伤亡。就算是必攻之城,也一定是三荒一攻四面包围,只攻一面城墙,只能证明攻城的将军并不愿意攻城,只是作秀而已。
陈安生心道安,“不知道这是哪个朝代?城外的敌人是哪国?”
医生仍在陈安生的头上忙碌着。首先,他用剃刀剃掉伤口周围的毛发,然后贴上黑色膏药。一股强烈的草药味飘进陈安生的鼻孔。陈安生忍不住打喷嚏。医生急忙拿着还没包扎好的绷带,没多久就包扎好了。
陈安生想说一声“谢谢”,却咬着牙忍住了。花了这么大力气才止住了20多年养成的小习惯。虽然说谢谢很简单,但难免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困惑和惊喜。这是/[k0/]不甘心,但最后他还是发自内心的说了声谢谢。
陈安生装作漫不经心的淡定问道:“我的伤怎么样了?”
军医官立即回禀,“将军,不要担心,没什么大碍。只要全神贯注于伤口,用不了几天伤口就会自然愈合。”
陈安生道安心里惊讶,“什么鬼?灵气?”
突然脑子里出现两个字,“修仙?”
军医官告别陈安生,陈安生点点头,看着军医官离开,脑子里又开始乱糟糟的。他抬头看了看城外各处的军阵,然后看了看军阵后面的远处。所有的山丘、树木和道路都变得模糊不清。只有那些在他身边忙着跑的士兵才那么真实,像真的梦一样。在他心里,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几个士兵提着水桶跑过来,水桶里装着清澈苦涩的井水。陈安生毫不犹豫的接过水桶,丝毫不在意士兵们惊讶的目光。士兵们看了看就跑了。普通士兵在高级军官面前总是胆怯。
陈安生放下水桶,蹲下来面对水桶,他紧紧闭上眼睛,双手捧水泼在脸上,苦涩的井水充分显示了它的作用,冰凉的井水顺着脸颊和脖子流到胸口。陈安生一个激灵,刺骨的寒冷刺激得他牙齿直打颤,他觉得自己清醒了很多,却没有睁开眼睛。
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从来不相信鬼神,所以他不相信修仙。他仍然希望这只是一个梦。他在心里默默地说:“马劳、恩斯、列宁告诉我,我只是做了一个梦!”
突然,他睁开眼睛,看到一桶原本清澈的井水已经变成了猩红色。他又站了起来。可惜什么都没变,古战场的场景还在眼前。
陈安生他把整个身子靠在女儿墙的城垛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静静地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无精打采,像一只被打败的斗鸡。
最后,他喃喃自语,他的声音几乎听不见,“好吧!我承认失败,至少我还活着,但我已经远离小蓝很久了。估计这个距离可以用千年来计算,而且是好几倍的距离。”
突然警戒的士兵喊道,“箭雨,箭雨,防御!防御!”并敲响了金锣,急促清脆的锣声传遍了城头,士兵们开始寻找掩体。
远处,天空中密密麻麻的黑点正在逼近,一阵猛烈的箭雨遮天蔽日,犹如壮观的飞蝗群。天空失去了颜色,太阳失去了光芒。士兵们拿起盾牌抵挡,或者蜷缩在栏杆边。
陈安生环顾这古战场的惨烈景象,看到箭雨就不想躲闪。他想,如果被箭射死,他还会回去吗?我能再见到小兰吗?他苦笑了一下,轻声说:“看来我还是不想放弃命运啊!”。
陈安生张开双臂,他准备拥抱箭雨了!
不远处的段烈鹏诧异的看着陈安生。当他看到陈安生面对箭雨的时候,他甚至张开了双臂。段烈鹏大惊失色地喊道:“陈都统,快躲起来!”
段烈鹏见陈安生不为所动,赶紧拿着大盾跑了过来。
这时候,另一个同袍刚好拿着一人高的盾牌跑了过来,把想死的陈安生拉进了盾牌的保护范围。段烈鹏也在这个时候赶到,两个护盾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防护盾。
“狗屎!你和燕王是亲戚吗?恨不得去死?”
说时迟那时快,话音刚落,箭雨终于倾泻而下,thunk thunk地面和铁包裹的盾牌,薄薄的地铁刚好没挡住从高处落下的箭。箭一只接一只地卡在盾牌上,箭尾不停地抖动。
陈安生终于醒悟了。他看着面前的人。他留着胡子,皮肤黝黑,脸上有麻子。胡子骂陈安生的时候,他整齐的白牙特别醒目,但是陈安生脑子里的第一个字只有两个字,“好丑!”
段烈鹏激动地说:“李度通,幸亏你来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李彤彤瞪了一眼段烈鹏,一巴掌拍下段烈鹏的头盔说道,“什么狗屁后果不堪设想?,呸!呸!呸!老子的弟弟李寿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怎么会迷失在这狗屁灵武城里!”
段烈鹏扶正了遮住一只眼睛的头盔,笑道:“小嘴笨手笨脚,不会说话,见谅。”
李寿道:“你小子可以,知道关键时刻保护大副是个料。总有一天我会请你的家人陈度推荐你做百夫长。”
段烈鹏笑着说,“这是下属应该做的。不升职不升职不升职!”
陈安生没好气地对段烈鹏说:“你还真把重要的事情说了三遍!”
段烈鹏瞬间尴尬,表情越来越委屈。他说不,哭不,走不,真的很亏。
陈安生我也觉得自己说话有点不厚道,一个一个的卖,以迁就情况。反正这个神仙自己也有一大堆,说:“别这么委屈,我又没说不推荐你,好好干,百夫长的位置也不是没有可能!”
画饼陈安生的功夫大家都熟悉,上辈子领导都是这么做的,就是让下属不失去工作热情,维护领导的威信,可以说是每次都在尝试。果然,段烈鹏听后连忙致谢,磕头重造,没算成本。
这时,李寿不耐烦地说:“好吧!好吧!走吧,我有话跟你说。”段烈鹏唱着“诺”,拿着盾牌走开了。
李寿哈哈大笑陈安生左右摇晃了几下。这样亲密的动作让陈安生一辈子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骂了一句“你有病啊?有病就去找军医官!”
李寿没有生气。他笑了。“陈安生,哈哈哈...我以为你真的挂了!远远看到你被石头炸弹打中,吓得我哥三魂七魄飞了出去。我们幼儿园的孤儿就剩我们俩了。你不能有事可做!"
“你怎么又成孤儿了?”陈安生狠狠的咬咬牙说,他现在完全清醒了,终于接受了现实,明白了目前的处境。这不是梦。
但是当我听到我还是一个孤儿的时候,我更加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大的倒霉蛋。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父母,就像我是一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
突然,一支箭轻易地从盾牌薄弱的地方射了进来,穿过了李寿的前臂。箭借着惯性继续深入,在李寿脸上留下了一道又长又深的伤口,鲜血流了一脸。箭尾颤动,发出嗡嗡的声音,伤口随着箭杆的颤动而疼痛。但如此剧烈的疼痛并没有让他放下盾牌,他一直举着盾牌保护陈安生和自己。
“啊!你说什么?”李寿咬着牙,折断了箭,问道。
“没什么……”
他旁边的一名士兵被从缺口射出的箭射中大腿。一阵剧痛让他失去了重心。他大叫一声,倒在地上。他的手本能地保护着大腿的伤口。不幸被另一箭射中颈部,鲜血飞溅,吐血不止。
士兵们的眼里满是惊恐的目光。士兵们一只手向陈安生伸出求救之手,看着陈安生渐渐变得空洞的眼睛,含糊不清地喊道:“全体...统一,帮助...帮帮我!”
陈安生立刻伸手抓住士兵的手,挣扎着要拽到自己面前,却不想士兵已经死了。陈安生还是一直抓着士兵的手,他也不松手。
李寿扔掉了断箭。他看着陈安生,眼里流露出深深的同情。他对陈安生说:“没关系,死球。今天你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会死很多。”
“我没死,但他死了。为什么……”
李寿不理他。这时,箭雨已经停了。他用一把长刀砍断箭杆,咬紧牙关忍受剧痛,将箭杆从手臂的血肉中拔出。血像泉水一样不断从伤口流出。
李寿的盾牌被扔到一边,他在地上的裹尸布上撕下一条布条胡乱包扎伤口。他看着陈安生,一边包扎伤口一边说:“听着,谁都不想死,死了就死了,就算没有那么多理由……”李寿皱着眉头继续笑着。罗晓还在等着我们俩回去呢!"
李寿拍了拍陈安生的脸,用坚毅的眼神给了他鼓励,拿起长刀,起身向城墙的另一个方向跑去,消失在混乱的人群中。
“谁是罗晓?”陈安生喃喃自语,但一声巨响打断了他的思绪。
太巧了!不幸的是,一颗石弹砸中了陈安生不远处的一个百夫长,他的脑袋一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无头的身体支着飞了出去。百夫长的盔甲基本上是萨格勒布的生铁制成的盔甲,防御力极强,剑很难伤人,但即便如此,如果被从空中飞来的石头炸弹击中,肯定会死,身体肯定会残缺不全。
“我的身体只是被石头炸弹的碎片击中,否则我没有机会复活。”
“暴徒又来袭击了!”一个站岗的士兵喊了一声,城内外战鼓声变得震天响。
“屠想要什么?这是哪国人?怎么没听说过?”陈安生我很惊讶。我想了好一阵子,没发现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少数。
“不会是南北朝吧?当时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除了著名的五华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少数民族。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但是这个巨大的城市外面的景象不应该是一个未知的民族!除了芜湖还有哪个民族能一次性出动数万大军?”陈安生越想越觉得奇怪。但这时候,敌人已经进攻了。他的精神已经恢复,他已经接受了现实。他必须咬紧牙关与城外的敌人战斗。毕竟在战场上,不是我杀,就是有人杀。
战场上,哀嚎尖叫,厮杀厮杀,弓弦破空,石弹轰然,云梯吱嘎,合奏曲成地狱魔音。
有的持矛,有的持弓箭,有的搬石头木头,有的抬伤员,有的喊指挥;有的面对懦弱,有的面对刚毅,有的东奔西跑,有的勇敢地冲锋陷阵;总之大家都在地狱边缘徘徊。
城外,进攻的军队不断地通过护城河桥冲过护城河,在远处的军阵后面,不断地用石弹和投石机跑上城墙。但这些投石机很少直接打在城面上,大部分都是直接飞入城内砸倒房屋,或者打在城墙上,立刻化为尘土。更多的石弹把自己的士兵打成碎片,溅起血花和血肉,一堆堆尸体像小山一样堆在城墙下,有的被砍死。
一个爬上女墙城垛的敌兵举起长刀,在陈安生处砍去。陈安生慌忙蹲下捡起地上的长枪,向前一刺,长枪穿透了士兵的皮甲,没入胸口。士兵口中喷血,猝不及防溅陈安生脸。血糊住了他的眼睛,陈安生急忙用手抹去了眼睛里的血。
战士用最后一口气举起了长刀。他咬紧牙关。他们很凶残。他想把长刀扔向陈安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1营营长马武冲了过来,只用一刀就把他的头砍了下来。士兵手中的长刀失去控制,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陈安生的眼睛恢复了视力,却看到敌人的脑袋带着飞溅的鲜血从他眼前飞过,最后倒在了地上。团长的眼睛还在盯着陈安生,充满了仇恨和不甘。尸体的脖子将鲜血喷向天空,仿佛要将天空染红,但最终,它还是无可奈何的倒在地上,斩断了血丝。
“怎么会?老虎的尸体吓到你了吗?冷血屠夫今天变成恶霸了吗?”那人被救了陈安生,眼神里流露出轻蔑,顺便讽刺陈安生。
“谢谢!”陈安生然后说。
这一声谢谢让马武大吃一惊,然后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马武说,他对着地上的无头尸体吐了口唾沫后,就不再理会陈安生,跑到另一个地方加入了战斗。
“这个人的萨格勒布盔甲和我穿的一样。段烈鹏说的是马武吗?哦!我真的不想处理这件事。看来以后得自己处理了,不过有机会我会离开部队的。”
城墙上的战斗继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陈安生不远处的城墙被蜂拥而至的敌人割开,5名敌人相继登上城墙。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官长蜂拥而上,一名背着盾牌的敌兵撞向炮阵。枪阵被砸了个洞,其他人也跟着砸。第一个撞进枪阵的中士一刀砍倒了拦住他的长炮手,然后转身砍倒了另一个长炮手。
指挥官涂兵saw 陈安生,saw 陈安生是将官。他眼睛一亮,觉得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马上举刀陈安生。此时,陈安生已经完全清醒,战斗是他的本能。当他看到胡涂持朴刀冲过来时,他拿起枪,刺向胡涂的石长大腿。胡涂世昌虚弱无力陈安生速度快,被陈安生射中大腿,大腿顿时血流如泉,双脚发软。
后面的一个敌兵看到自己受伤想伸手救同伴,却被旁边的守城兵砍断了看着拿盾牌的手臂,随后被子弹打死在腰腹。其他想打仗的士兵突然失去了突入点和保护点,进攻受挫。涌出来的长枪兵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打死。
这边战斗刚结束,另一边突然有个霸气的敌人从城墙垛上爬了上来,喊着“杀”,高举长刀正要跳下垛,陈安生没多看他一眼,顺手把长枪扔了出去。陈安生我惊讶地发现,当他把长铁枪扔出去的时候,体内有一股能量涌动,长铁枪飞了出去。
“这是?”陈安生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手掌,惊叹于自己强大的力量,他看着突如其来的敌人。
长枪直接刺入敌人的胸膛,强大的能量带着长枪穿过锁甲进入胸膛。敌人口中毫无意义的喊杀声戛然而止。长枪的力量还远没有结束,它带着敌兵的尸体飞到了城外。
长枪手冲向城垛,试图堵住防守的缺口。谁知人还没到,一个壮如牛的大汉跳上一个生铁做的黑色半盘。他比普通人高出两个头,有着像一种龙一样粗壮而宽阔的全身肌肉。棕黑色的脸颤抖着,眼睛变红,怒目而视,就像佛前的金刚。
他抓起还没飞远的长枪,把身体往后拉,奋力打向一群长枪手。身体脱离长枪,两个反应迟钝的士兵被砸飞。手里的长枪掉了下来,身体撞在身后的城垛上,口吐鲜血,剧烈的疼痛让他们连声音都喊不出来,很快就昏了过去。
陈安生只见胡涂将军一挥开矛,划过扇形的矛尖,破空而来。陈安生他在长枪手后面的安全区域。看到危险逼近,他探出身子,用爪子抓住面前的两个士兵,用力向后一拉。然而,还有另外两个人被总司令从胸部砍成两半。被砍成两半的士兵没有立即死亡。身体的残肢在不停地抖动,鲜血四溅,聚成一片洼地,不断地尖叫出痛苦的声音,在地上抓手,寻找救命的稻草,半个树干在地上拖着深深的血痕,生命在剧烈的痛苦中慢慢过去。
屠将军的长枪在完成使命后离开了他的手掌,毫无留恋地飞出了城。屠将军拔出一把沉甸甸的大刀,刀身漆黑,只有刀刃泛着银白色的寒光,像是很久没有喝过血的妖兵,流露出对鲜血的渴望。

 已完结
已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