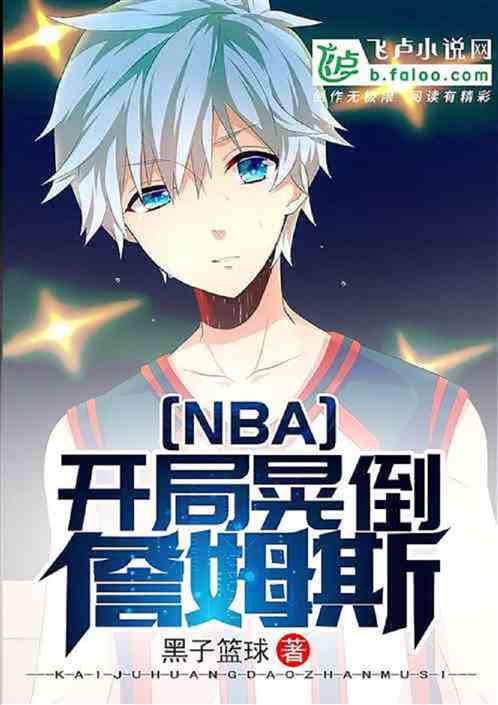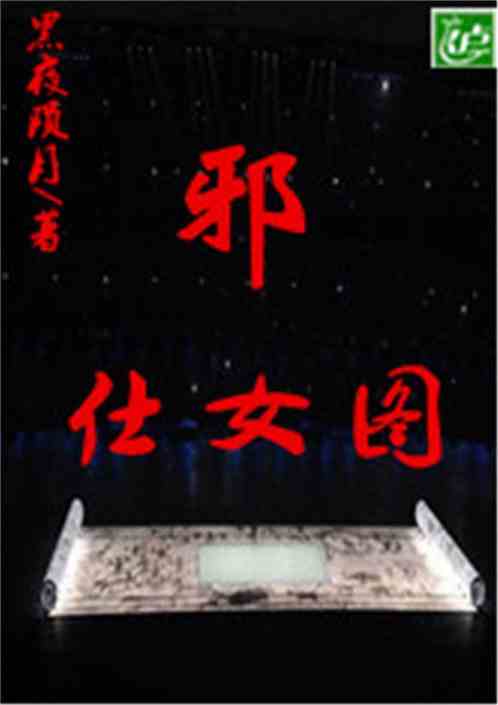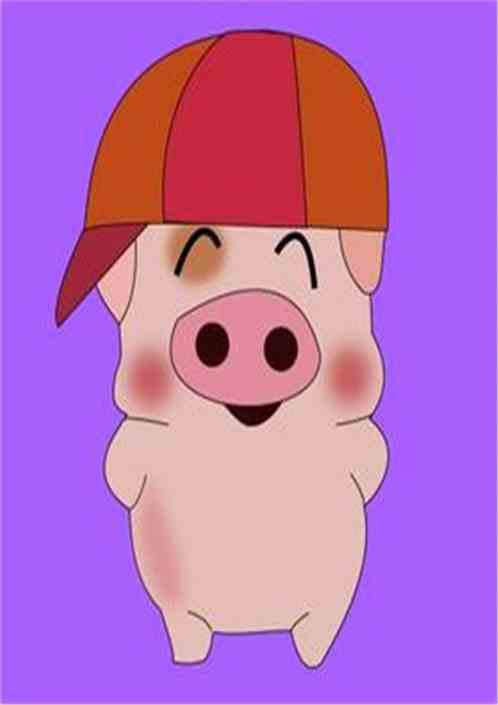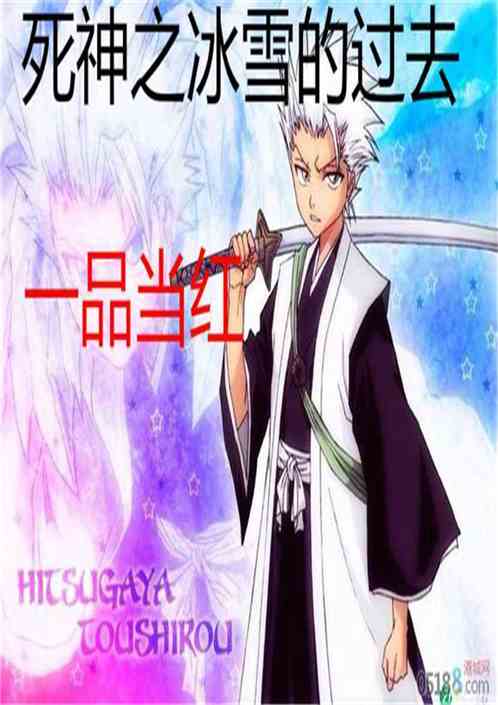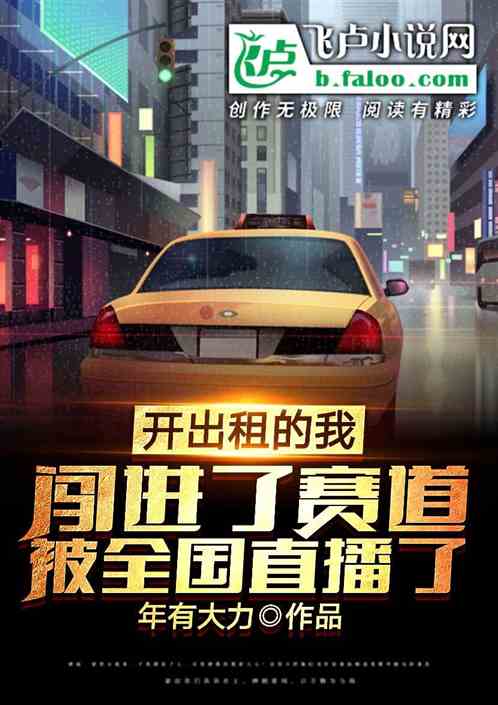十二、断枝枯火——我是这个世界上可笑的客人,斟酒已久。
“人生如晤,若如当年;
生活是一样的,如果你再也看不到它;
你所看到的生活,一言不发;
人生无言...
反对金扇在抖落风流砚台..."
有人在唱歌,夜很黑,风吹过窗外的树叶有沙沙的声音。
教室里稀稀拉拉的站着几个人,白炽灯亮着,我趴在桌子上打瞌睡,眼前的光线很宏大但也很模糊,模糊而朦胧,像是眯着眼睛看世界后在哭泣的人。我试图直起身子,但我尽力弯曲我的手指。
便衣的女孩走到门口,扶着门框往里看:“……在哪?”
我听不清她在说谁的名字,也看不清她的脸。一切都在我眼前变成了淡淡的光晕。
下一刻,太阳来了。
我坐在台阶上,女孩蹲在院子中间逗着跳跃的鱼儿。逆着光线,整个人被笼罩在太阳的金色光芒中。
这不是我熟悉的研究所或者二层小楼前的院子,而是一个更安静更寒冷的地方。地上覆盖着积雪,远处平坦荒凉,一片荒芜。最后,阻挡一切的是高耸入云的群山。
世界笼罩在白色之中。
“原来你在这里。”我说。
她举起手在空中挥舞。
这个梦在我无意识的日子里重复了无数次,但我一次也没见过她的脸。
二月十五日。
龙抬头的那一天,是最后一股侵袭方圆地区的寒流。冬天来自海洋的寒流,几个月前莫名其妙的风暴,一切都不正常。但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什么也猜不到。
之后天气一直很好,气温上升很快,阳光充足,再也没有下过雪。
我看着窗外的风景发呆,就像几个月前在招待所醒来一样。
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却永远不会有一个便衣女孩伸手到我的额头。
“智慧。”纪在他身边喊道,“出院手续已经完成。走吧?”
我点点头。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无论我如何调动自己的情绪,我都察觉不到胸中那种闷烧不安的感觉。随之而来的力量就像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无论我怎么哀求,都没有回音,也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产生的。
就像另一个人一样,他撕开了时空的缝隙,在暴风雪中走下了银色的王座。
像神一样的人。
“医生说你的大脑仍然充血。出院后就不要训练了。”纪手里拿着包走下台阶,我跟在他后面点了点头,意识到他看不见,又给了一个嗯。
其实我对训练也没什么想法。躺了十天总觉得懒。虽然我没有继承主角的光环,但是我继承了主角的萧蔷体质,那种打不死,而且可以很快的愈合伤口的体质。
“你最近话不多。”他说:“整个人变得沉默。”
“我没怎么说话。”
“开什么玩笑?”纪笑道:
“我是认真的。我这人没劲,经常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不然我上辈子也掩饰不了自卑,装冷。
“其实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会害怕,但事到临头,我觉得就是这样。别人把我打得头破血流,不过是微微一皱眉。我的怒火一点点膨胀起来,我甚至懒得反击。没有我特别讨厌的,也没有我特别喜欢的。”
如果有人觉得有,那一定是我故意展示的伪装,让他放松警惕,让你觉得我是一个普通正常的人。无脑,神经粗,感情白痴,对世界无知,思想开放,都是我最常用的伪装。对我来说,我只需要适当的装疯卖傻。也许我有时候心血来潮做一些疯狂的事,但那只是自我满足,因为我想做。
毕竟我之前的生活跟停很像。
包括我虽然极力掩饰自己的越轨行为,但还是比普通人得到更多的关注。
我觉得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还是脱离日常生活。
这是一种天然的非日常吸引,我并不排斥。
至少他们能激起我的一点点激情和好奇心,不会让我太无聊,所以来到这个世界后我还是挺平静的。
只是有点孤独。
“那么那天晚上你痛打严阵他们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纪说,他跟我说燕真是水师榜上一个麻烦的家伙。那天晚上,喷火龙带我回去了。我躺在它的背上,每一只野兽都浑身是血。
我沉默了很久,没有给出答案。不是想不出答案,而是觉得太搞笑了。
我是个得过且过的人,但在龙抬头的那一天,心里确实有一种没人能阻止我的自信。
我要救那个救了我很多次的女孩。我想让她走。我想让她看到世界的广阔。我想让她得到她想要的然后逃走。我想给她她想要却得不到的一切。
但除了自己的生活,我一无所有。
那我们就要用生命去战斗!就算你手里拿不住剑,也要用钉齿撕裂他的喉咙!
我以命搏命,谁敢挡我的路就死定了!
没人能...冒犯我!
“智慧...?"好像在很远的地方,有人在低声呼唤我的名字。
突然,我回过神来,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仿佛某个只剧烈运动过的人把衬衫都湿透了。
“你怎么了?突然不动了。”纪在我面前挥了挥手。“我以为你又要突然昏过去了。”
“我很好。”我把手放在额头上,依然恍惚。
“真的没事?”
“真的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我说,“我要去镇上转转。”
“但是医生说……”
“医生还说吃牛肉导致疯牛病,吃猪肉导致口蹄疫。不吃不喝做神仙?”
他掐了我一下,耸耸肩就走了。
其实小镇并没有特别大的损失,除了场地已经化为灰烬,其他地方的火势在蔓延之前都得到了控制。这都是因为索洛依的雨天。水军舰队虽然分散克制,但还是把熔岩团压制在了自己的地盘上。我总觉得这个女人胆大心细,不像巴图尔说的那么狂妄自大。
一路到中央公园,我坐在长椅上,抱着头缩成一只虾。
刚刚自焚的心情突然回来了,还没等我意识到,就在心里和脑海里肆虐起来。冲动的年轻精神自然地、突然地扭曲成不可侵犯的威严。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喂,你。”光线暗了下来,有人推了一下我的肩膀。
“哦...你……”我抬头看着笼罩在我头上的阴影,突然想到了一些。“那天是你找我麻烦的。”1月8日,还没出手就被停止吓跑的三人组,今天又出现在我面前。其实我也不记得他记仇什么的,不过对了,脑子自然记得,没办法。
领导环顾四周。“那……今天的女人呢!”
“她不在这里。”我老老实实的回答,此刻不想浪费脑细胞。
“很好。”他立刻变得傲慢起来,踢了我一脚。我扑倒在一边,脚后跟擦到了我的腰,还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立刻感到火辣辣的疼痛。
三个人围着板凳,左右前方路线被封锁,唯一的后方被椅背封锁。我还是坐着,实在忍不住了。领导抓住我的后颈,把我踩死在板凳上,用鞋尖踢我的腹部,枪伤裂开了。我试图蜷缩起来,握紧拳头。
每当一点点权力显露出来,即使没有冤屈或敌意,也可以施加暴力。人就是这么直白恶毒的生物。
"...照顾好自己,下次有人烦你我就不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和我分手,担心和掩护我的冲锋陷阵。但是当我以为这样的离别永远不会把我们分开的时候,真正的离别已经悄然而至。现在真的是天各一方,没有人会来救我。
想起当时在海里的风风雨雨,她一拳打在我的鼻子上,生气地骂我,把我拖上龙背,轻声说“别哭”。
我一直以为知止和我一样傲慢任性,但这时我发现她从来没有麻木过。那个女孩一直致力于任侠的仗义。她只是把一切都藏在眼里像雪花飘落一样的冰冷和疏离里,像你站在温暖的房子窗前看着雪花飘落。世界寂静而温柔。
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感到心中巨大的愤怒。总有一天,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什么都不会,就会对自己特别反感。当你意识到自己的邪恶时,你会比恨自己更恨自己。我想站起来,好像只要发现手里有一根枯枝,就可以学古代的侠客,用剑杀人。
可是我不能,我只能点燃它,化为火花,等着改天燎原。
“你……离我远点……!”我忍住因为疼痛而颤抖的声音,一点一点地挤出话来,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我怒吼着翻身,把板凳撞向一边,翻倒在地。
我蜷缩在椅背、座椅和地面的空隙中,突然撑起身子趴在地上,翻过椅子,一拳打在对方喉咙上。力壮鸡被释放,吓跑了另一个敌人。
从今以后,我所有的敌人,所有给我造成痛苦和苦难的人,都要被我自己一拳打回去,我的恩情或仇恨都要十倍奉还给你!!
压住我的被自己拆了,绊倒我的被自己推翻了。你认为...你认为...
“我真不明白这些人是怎么想的,认为没有李晟我就不能成功吗?」
“你以为我不停车就什么都做不了!!"我怒吼着扑了出去,第三个人慌乱中打开弹簧刀,向我刺来。我看到了,但我不想在乎。有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回荡,而且是不可抗拒的。这不是我的声音,像是上帝的启示。
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这份遗嘱。它激情四射,大喊大叫,拼命催促我,说谁冒犯你就死定了!因为你失去了,你会得到的!!
“湍流!”街对面传来一个非常随意的命令。浑浊的水柱打在奔跑的优雅猫身上,水系训练师手中反复被打的第三人怒喝一声,放出了自己的怪物。
“我想念我的头槌!”刚刚出现在战场上的优雅猫,当场打滚,身体前倾,冲向对面的短吻鳄。他的动作真的一点也不优雅...
街对面,黑衣少年懒洋洋地抄着口袋,靠在路灯柱上,干脆连个命令都没下。
短吻鳄的右脚后撤,然后上前一拳打出,优雅猫顶在上面。如果这是一场游戏,你可能会看到优雅猫的血液低谷迅速触底。他吹了声口哨,直起身来,走了过来。怪物顺着少年的肩颈,一手按住猫一样的PM,扔到一边。
粗暴的攻击方式,不在乎任何不是自己的东西。
“妈的……都是疯了。”领头的低声啐了一口,领着两个跟班掉头就跑。
我没有追,新来的也没有。他站在我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坐在地上的我。
在我的眼前,黑衣青年的头发是红色的,深红色的,即使在阳光下,也呈现出一种又黑又重的感觉,像凝固的血液。
这样暗沉的颜色显然让我想起了新鲜的衣服和马。
有些人天生自负骄傲,会给自己最张扬的少年时代,在阳光下咆哮,或在夜空中咆哮,粉碎一切他不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从不怀疑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的脚步。它们并不完全明亮,但它们可以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大声歌唱。
银银。我记得这个表情。
显然,他就是这样的少年。虽然他父亲的火箭队被红方折腾的很厉害,甚至连老巢都叫到了尽头,但都不在他的关注范围之内。父亲的,家庭的,还有他的,只是他的。他有力量和信心,不让任何东西阻碍他的脚步,藐视家人和家族给予的权威和财富,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更何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剩下的火箭就是一股大力量,追在他屁股后面收拾他的烂摊子。
多么令人羡慕的光环。
“你是谁?”我不确定池是否认识这位少爷,只好装作不认识。
“被打傻了?”他直视着我,问龙抬头的那天好像是什么战斗。
“谁知道呢?”不仅被打傻了,还被打傻了逼。我在心里讽刺道。
“你以前去过哪里?那时候你还没那么弱,只有一腔无用可笑的气。”
“谁知道呢?”我重复道:“也许已经死了,或者被我遗忘了。”
他抓住我的衣领,几乎把整张脸都翘了起来,盯着我看。
“死亡是不可能的,你现在活得很好。既然忘了,我再跟你说一遍。”

 已完结
已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