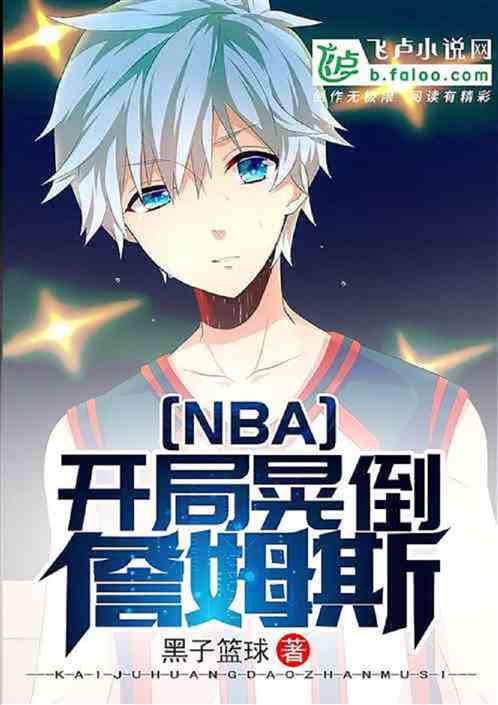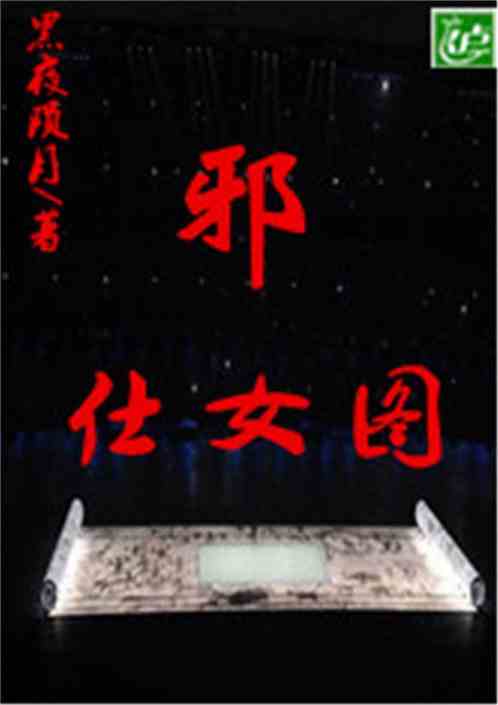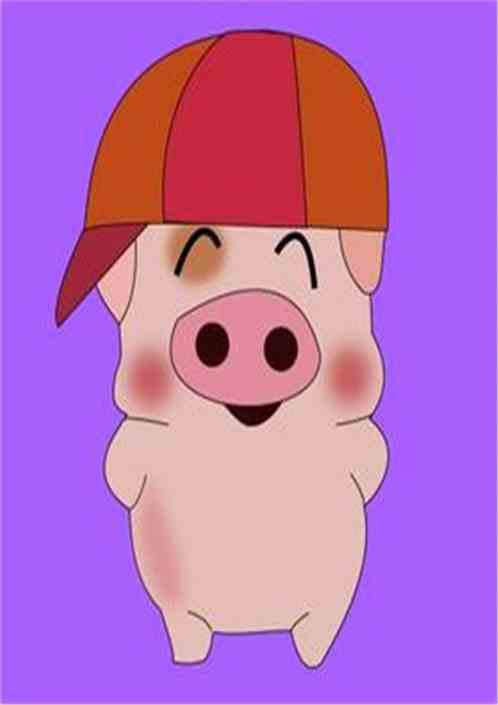瑞士伯尔尼州。
在寒武纪酒店高大清晰的落地窗前,阿尔卑斯山一览无余。热气腾腾的温泉池里漂浮着固定的皮垫,里面放着鲜嫩鲜亮的反季节水果和烤得酥脆的松香面包。
房间里的女人穿着白色丝绸浴袍,头上戴着紫色浴帽。半躺在柔软的贵妃椅上,我感到一种难得的快感。贵妃椅对面的小长桌摆满了美食。她呷了一口装满草莓利口酒的香槟酒杯,拿起最新的八卦杂志打开。头版头条新闻让她笑得连连摇头:“独家!著名女企业家钟将于次日抵达荷兰接受安乐死。
她喃喃自语道:“消息不错。但要去的地方是瑞士。”
合上杂志,钟打开了手机的相机,调成了前置模式,把红酒杯放在自己脸上,眨了眨眼睛。把相机调回来,找个好角度,把面前的食物拍下来。打开微博,配文:好好生活。发送。
做完这一切后,她突然感到筋疲力尽。看着好评和评论的激增,她并没有兴奋地去查看。点开相册,刚才那张随意精致的照片也陷入了近期删除。
她完全瘫在贵妃椅上,像一潭沼泽,毫无生气。裹在头上的浴帽塌了,散落着一根半干的头发。
压抑了一会儿,她还是设法爬起来去卫生间吹头发。半湿的头发在她手中轻盈舞动,很快变成蓬松柔软的干发。她把一个肉丸放在胳膊上,回房间换衣服,然后回来。
镜子前的女人只有二十五岁,却累了一倍。她穿着宽松的灰色针织薄毛衣,丸子头比以往更漂亮。碎发散乱,一枝淑女烟在手,吐气如兰。裸露的手腕和脖子上覆盖着皮肤和积雪。目前有淡蓝色的黑眼圈,眼神有些呆滞,但难掩她明亮动人的脸庞。她的胳膊向前撑着,靠在脸盆架上,头向前拉着。干净的下颌线和肩颈线都显示出了她的精致和纤瘦。前倾的动作,腰部紧贴脸盆架,让毛衣紧贴上身,露出傲人的曲线。
钟把烟头掐灭在墙角的烟灰缸里,捋着背上的碎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黑眼圈,也有淡淡的法令纹。我看起来不像25岁的女孩。
她无奈地笑了笑。再看,那些表明自己不再年轻的沟壑和沟壑,不会消失。这些都是抑郁症的影响。
钟几乎忘了她以前是多么精力充沛。好像永远不会累,对生活永远充满热情和幻想。
“转眼间,已经八年了。”她伸出手抚摸镜中人的脸,反复擦拭她的皱纹,好像它们会消失。
第二天,瑞士巴塞尔
为了迎接这一天,钟已经花了半年时间。
正如八卦杂志所说,她将被安乐死。
她患严重抑郁症六年了。花了几百万人民币才得到安乐死的机会。
钟被安全地抬上了手术台,平静地看着药物一点一点地注入静脉。
眼神越来越模糊,恍惚中,她想起了自己十七岁的时候。
这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17岁的钟既聪明又漂亮。高二提前考上高校,一举获得校花称号,家境不错,无忧无虑…
她用最后的力气,用胸膛撕开了一个微笑,最后闭上了眼睛。
陷入黑暗
很长一段时间,四肢有触电般的麻木。
“就像老式电视机的雪花屏”,钟的脑海里突然蹦出这么一个抽象的比喻。
很快她就意识到不对劲了。她的手脚不像手术台上的位置。她不是已经注射安乐死了吗?她怎么会有意识?
她试探性地睁开眼睛。在我面前的是一张美丽精致的俊脸:一双微微上扬的丹凤眼充满了不耐烦,白皙的皮肤,硬朗的五官,就像来自漫画的人物。
“起来。”少年吐出两个短音节。声音沙哑,语气中充满了不耐烦。右手的手肘支在她的桌面上,中指的指关节不停地敲打着桌面。
钟连忙直起身子,想离开,可是双腿却像被千万只蚂蚁咬了一样难受。又麻又痛,还有点痒,但我没办法,只能解释:“我的腿麻了。可能是抽筋了。”
看着钟无辜的眼神,少年停止了说话,冷哼一声,拿着书包在她身边坐下。摊开一张崭新的纸,开始写吧。钟一眼就发现那是他们的暑假作业。
双腿的麻木感过去后,钟才认真地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她学生时代本该睡觉的手术台变成了木桌,上面堆满了笔记本和试卷,眼前出现了一块熟悉的黑板,上面写着未完成的粉笔字迹:二年级三班。墙上挂着一些老式的红边碟钟,旁边还贴着“奋斗”二字。
她使劲捏她的小腿。很疼。她不是在做梦。
她回到了17岁。
只是和记忆中的还是不一样。比如那个身材匀称的大树旁边的美少年,明显和同学不是一个画风。比如收音机断断续续放了好几年的歌,极其清晰,像3D环绕,只有她说话的时候才停下来。这就像...为她准备的特别背景音乐。
莫名其妙的心慌,她进厕所洗了把脸,冷静下来。拧开水龙头,她记得,水龙头先是像喷泉一样喷得到处都是,两秒钟后又变回涓涓细流。她用手捧着水。
在她把脸埋进手掌的那一刻,时间凝固了。她的脑海中出现了清晰的机器人声音,还有一段字幕:“祝贺您成功进入我们软件的内测阶段。这是你为你收藏列表里的歌曲脑补制作的mv图。你是这里的女主角。请大家大胆发挥想象力,在贴合歌词核心的前提下,尽快完成mv创作。”
"..."钟一时无法接受这个离奇的事实。“你知道我听音乐的时候在想什么吗?”
那个机械的声音停顿了一下,好像在解释如何让她不处于社交死亡的状态。过了很久,她决定说实话:“是的。”
或许我觉得这个解释太直白了,我补充了一句安慰的话:“但是你也是重生的。只要你把你歌单的故事讲完,你又可以为自己而活了。”
“为自己活一次。”这句话对钟来说太有诱惑力了。她多么想重新开始,她现在多么幸福。钟试着跳起来。曾经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病体,现在毫无压力地蹦蹦跳跳。她捂着嘴,以维持自己端庄自持的未来女企业家形象。
稍微冷静了一下,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女企业家钟矜持地笑了笑,决定投桃报李——毕竟她是独生女,父亲的钱以后都是她的,先花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你是哪个公司的?”
机械的声音沉默了一会儿,坦白地坦白道:“江淮音乐。以后都是你开的。”
轮到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想通了:“不浪费钱,不浪费钱”。他的语气就像一个不识字的老人知道自己心爱的孙女考上了清华北大一样安慰。
-
她走进教室,开心地捅了捅同桌的男生:“我叫钟。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刚填完试卷,心情很好。他淡淡地看了她一眼:“依桐。”看到钟,也一脸不解地眨了眨眼,然后撕下试卷的空白一角,刷上自己的名字,推到她面前。
钟把它放在一个珍贵的地方,压在他的铅笔盒底部。想了想,觉得不妥,就去把姓名标签,塞进名片的背面——这是她重生的证据,一定要好好保管。
看着钟那庄严而近乎神圣的表情,他突然被感动了,难过了。
自从我妈去世后,没有人把他的事情看得这么重,哪怕人家是装的,或者她对谁都是这样——仿佛一切都是上天的恩赐。
他起身要走。临走前,回过头来,第一次仔细打量了钟一眼。
17岁的钟很漂亮,皮肤白皙,头骨很发达,小而圆。鹅蛋脸,下颌线条清晰流畅,高高的脖子,一双灵动清澈的圆鹿眼,窄窄的扇形双眼皮,微鼓的蚕泛着粉红色,中庭,人和下巴都短而小,眉毛不把自己涂成黑色,嘴唇不把自己涂成红色。嘴唇肉肉的,看起来软软的,好亲。嘴角下方有一颗小痣,辨识度很高。
“钟千千。”他愣了一下,粗粗的街道上下翻滚,仿佛在努力消化这三个字。“我记得你。”
说完就走了,留下钟一个人在座位上。
“他应该是无害的。”钟对眨了眨眼。“我也记得你。”
“千千,回家吧。”熟悉的声音把钟纷乱的思绪拉了回来。她看着眼前可爱的女孩,忍不住把她抱在怀里。
那是她最好的朋友,谢幼玲。
上辈子的谢幼玲因为校园暴力得了厌食症,1米7的人只有70多斤。当时她是提前考上高校后申请在家自学的,谢幼玲也从来不想给别人带来负能量。
“我好想你。”钟像只树袋熊一样挂在谢幼玲身上。她身上的温暖和踏实,钟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了。
“回家吧。”谢幼玲像抚摸婴儿一样抚摸着她的背。虽然心里有疑惑,但我绝不会多问,只会轻声安慰你。
只有在她身边,钟才能卸下所有的防备,安心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已完结
已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