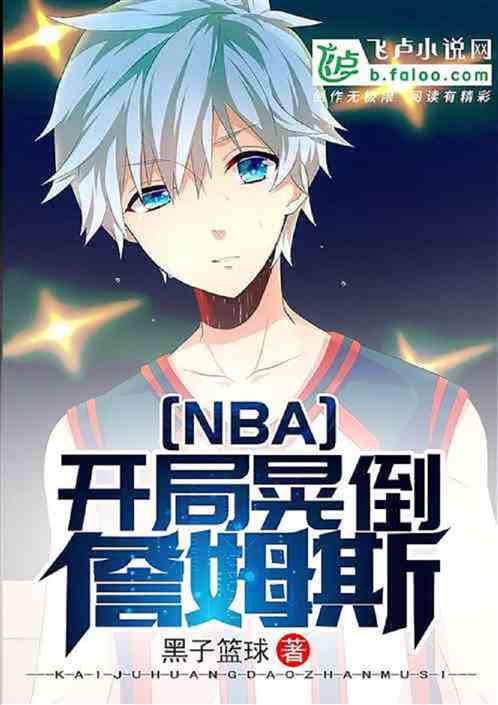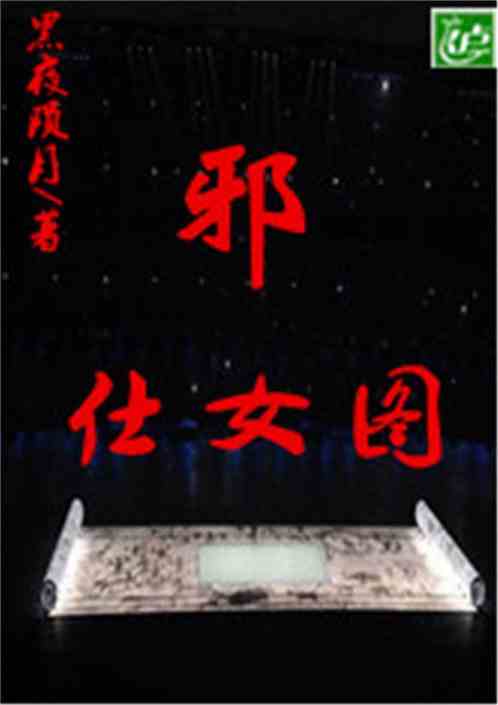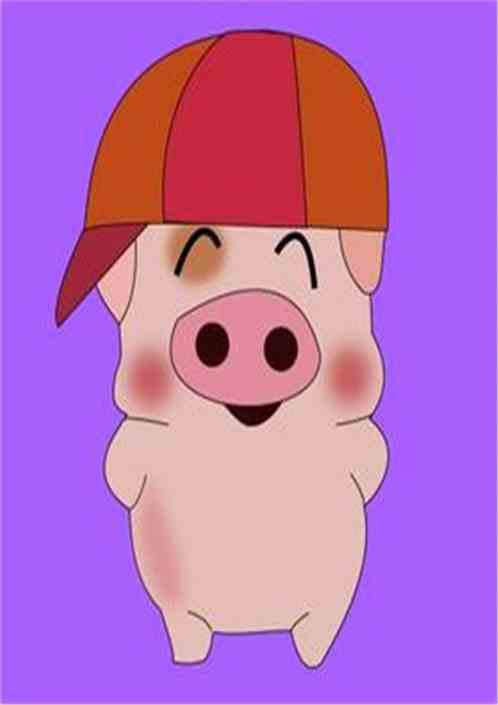离县城50公里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寨子,那里的中老年人大多重男轻女。我父母的婚姻是双方父母(我爷爷奶奶)包办的,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婚前从未谋面,只是媒人充当中介,传达双方的意思。作为媒人,我给男方做了媒人(我父亲)。这是一段有尊严、有权威、有效力的婚姻,被父母称为媒人之言。
我妈父亲相识于198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父亲带着我妈给亲戚朋友敬茶,那天正好是他们的婚期。一年后,我姐出生了,我奶奶给我妈煮鸡蛋。第二年,二姐出生,奶奶给妈妈煮鸡蛋,村里却开始有了流言蜚语。第四年,三姐出生,奶奶给妈妈煮鸡蛋。村里的流言蜚语从村长传到了村长。第六年,四姐出生,奶奶给妈妈煮鸡蛋。村里的小道消息从村长传到了村尾。第八年,1996年出生。我奶奶给我妈炖鸡汤,村里的小道消息就传遍了全村,甚至传到了隔壁村。“怎么又是女生?”来自父亲灵魂深处的疑问。
过了两天,村里一个老婆婆找到我父亲,告诉我父亲隔壁村的二姨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说我妈前两天刚生了另一个女儿,也就是我,问父亲愿不愿意给她。我父亲坐在地上用水桶抽着烟草。随着父亲嘴里吐出的烟草的烟雾,父亲慢慢吐出三个字:拿走。奶奶满意地回去告诉了结果。第二天,隔壁村的二姨来抱我。一拿起来离开妈妈的怀抱,我就哭了,妈妈剧痛着从床上爬起来,试图保护我。看着刚出生没几天的我,父亲有点惋惜。奶奶也来保护我,说就算有米汤也要养我,这样我就被保护了。
家里五个女孩,重男轻女的思想下生活压力大。正是因为这种无形的压力,我父亲才犹豫着挥手让父亲说出那三个字。我爷爷是外地搬来的,但我三姐出生没几天,他就开车西去了。我祖父去世前喜欢戏弄我的姐妹们。他不认为男生和女生是一样的,我奶奶也是。即便如此,他最终也无法克服那些话带来的无形伤害。
随着一声哇,我渐渐长大了,会爬,会走,会跑。随着我们五个女孩的成长,大姐和二姐面临上学,家里的经济压力从无形变成了畸形。一岁多的时候,父母外出打工。我的五个姐姐和我奶奶住在一起,我奶奶走到哪里都背着我。大姐和二姐去最近的破旧学校上小学,奶奶在家背着我带着三姐和四姐做饭做家务。一部老式的按键式手机,是奶奶和父母之间唯一的桥梁,所有的苦乐都通过这座桥梁诉说给对方听。
那是因为我们还年轻,不知道什么是思念。过年是我们最期待的一天,因为过年有压岁钱,有好吃的,有小鞭炮。第一年爸妈出去打工,过年没回来,就给奶奶点钱给我们买点好吃的过年。当时只听说是过年。奶奶早早起来,去镇上唯一的邮政储蓄银行排队取钱。随着夜晚的到来,点上蜡烛,奶奶煎了五个荷包蛋,蒸了一碗石磨玉米饭,煮了一碗红豆酸菜汤过年。
我的父母第二年回来看望我的祖父母。因为我经常哭,三姐调皮,四姐温柔,所以爸妈打算带着我和三姐,把她送到爷爷奶奶家。奶奶在家陪大姐二姐一个人上学。父母在省城一家饲料厂上班,带着我和三姐。据我妈说,我小时候很爱哭。我哄不好它。他们甚至请人给我算命,让我去见米歇尔·普拉蒂尼。我还是爱哭。所以,父亲只好每天背着我,直到弟弟出生。

 已完结
已完结